妈妈总说:“你得学几道菜,不然以后怎么办?”我每次都敷衍:“会煮面饿不死就行。”
转变发生在去年腊月二十八。妈妈在厨房准备年货时突然头晕,血压升高。医生说需要静养,不能劳累。看着妈妈苍白的脸,再看看冷清的厨房,我第一次感到恐慌——年夜饭怎么办?
“今年我来做吧。”这话脱口而出时,我自己都吓了一跳。
妈妈惊讶地看着我,眼里有怀疑,更多的是欣慰:“你行吗?”
“不就是几个菜嘛。”我嘴上硬气,心里直打鼓。
第二天一早,妈妈坐在厨房门口的小板凳上,开始了我们的特训。第一道菜是红烧肉。
“先切块,不要太小,会缩水。”妈妈的声音从身后传来。
我拿起刀,手在抖。那块五花肉在案板上滑来滑去,根本不听使唤。切出来的肉块大大小小,有的像麻将,有的像饼干。
“没关系,第一次都这样。”妈妈笑了,“热锅凉油,放冰糖。”
冰糖在油里噼啪作响,我躲得老远。等糖色变成枣红色,该下肉了——我却犹豫着不敢靠近油锅。
“快翻几下,不然会糊。”妈妈提醒。
我冲过去胡乱翻炒,油星溅到手背上,烫得我直甩手。再看锅里的肉,有的已经焦黑,有的还带着生白色。
“火太大了。”妈妈摇摇头,“做菜急不得,要用心感受火候。”
第二次做红烧肉,我学会了耐心。看着冰糖慢慢融化,变成美丽的琥珀色;闻着肉香从腥到香的变化;听着汤汁从剧烈沸腾到温柔咕嘟。当那盘色泽红亮、肥而不腻的红烧肉端上桌时,妈妈尝了一口,眼睛亮了:“就是这个味道。”
接下来是清蒸鱼。妈妈说这是年夜饭必备,“年年有余”。
“鱼要选新鲜的,鳞要刮干净。”她坐在那里指导,“肚子里那层黑膜一定要去掉,那是腥味的来源。”
我笨拙地刮鳞,鱼滑溜溜的,总是从手里逃走。开膛破肚时更是手忙脚乱,鱼胆差点弄破——妈妈说那会让整条鱼变苦。
最考验技术的是在鱼身上划刀。“不能太深,也不能太浅,要刚好到骨头。”妈妈比划着,“这样蒸的时候才入味。”
蒸鱼的时间要精确到秒。“水开后放进去,大火八分钟。多一分钟就老,少一分钟不熟。”
八分钟后,掀开锅盖,鱼肉刚好绽开如花瓣。淋上蒸鱼豉油和热油,“刺啦”一声——那是年夜饭最动听的声音。
学做蛋饺时,我彻底体会到了什么叫“一看就会,一学就废”。
小勺在火上烤热,抹一层油,倒蛋液,转动勺子形成蛋皮,放肉馅,趁蛋液未完全凝固对折封边——说起来简单,可我做的蛋饺不是破皮就是露馅,奇形怪状得像抽象画。
妈妈接过勺子示范:“手腕要柔,转动要匀。”她的动作行云流水,一勺蛋液在她手里变成金黄的月牙。
我试了二十多次,终于做出一个像样的。那个傍晚,我们娘俩一个教一个学,做了六十个蛋饺。虽然最后只有四十个能看,但妈妈把它们都收进了砂锅里:“这些都是你的勋章。”
年三十那天,我从早上八点就开始忙活。妈妈时不时来厨房门口看看,但很克制地没有插手。系着她的旧围裙,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传承——不仅是菜谱的传递,更是一个家的味道在延续。
下午四点,最后一道菜上桌:红烧肉油光发亮,清蒸鱼形态完美,蛋饺在砂锅里咕嘟,翠绿的青菜衬着雪白的年糕,鸡汤冒着热气。整整十道菜,取十全十美之意。
爸爸扶着妈妈入席时,她看着满桌的菜,眼眶红了:“我的孩子真的长大了。”
那一刻,我突然明白,学做菜不是为了填饱肚子,是为了在重要的时刻,能为爱的人撑起一片天。就像妈妈用三十年如一日的一日三餐,守护着这个家。
现在,我已经学会了很多拿手菜。但最珍贵的,是学做菜过程中那些温馨的时刻——妈妈握着我的手教我切菜,我笨手笨脚地把糖当成盐时她的笑声,还有她尝到我第一次成功的红烧肉时,那满足的表情。
厨房还是那个厨房,但对我来说,它不再是个陌生的地方。那里有妈妈教给我的不只是做菜的技巧,更是对生活的热爱,对家人的用心。每当系上围裙,我都能感受到妈妈就在身边,用她温柔的目光,守护着我在灶台前的每一次尝试。
今年的年夜饭,依然由我来做。不过这次,我要创新一道菜——在妈妈的红烧肉里,加入我自己的理解。我想,这就是传承最美好的样子:在接受中创新,在继承中发展,让家的味道,一代代飘香。
未经允许不得转载:百图曝光网 » 内容均为网友投稿,不排除杜撰可能,仅可一观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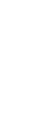 百图曝光网
百图曝光网
热门排行
阅读 (123)
1在跨境电商做选品:从踩坑滞销到爆单的选品逻辑阅读 (119)
2市场调研助理:协助项目的问卷整理阅读 (108)
3面包厂工人:给刚出炉的面包贴生产日期标签阅读 (106)
448岁做直播卖水果,一开始没人看,后来靠真实试吃涨粉卖货阅读 (105)
5明知没有结果 可心疼还在继续